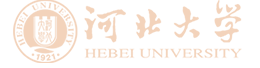黑马关于《四世同堂》回译的回忆
发布时间:2020-10-11 17:57:24
毕冰宾

2017年,我有机会将老舍先生杰作《四世同堂》中文稿佚失部分的英文稿译回中文出版,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这几个月的翻译过程,可以说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做的是字句替换和寻觅可能的老北京话的游戏,也做了一个回到80年前的老北京生活的梦。我“扮演”了老舍,也与书里的老北京小羊圈胡同的人们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
《四世同堂》命运的一波三折
2017年初在网上看到消息云,《四世同堂》这部小说在没有完全出版中文版前已经在美国全部翻译成了英文,是老舍先生口授、美国译者浦爱德在打字机上打出的英文译稿。除非作者本人有能力亲自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文,老舍与浦爱德这样的合作翻译应该是文学翻译的最佳典范。相信翻译过程中他们会有所切磋,达成默契后才定稿的。这等于作者最大限度地参与了翻译,对英文译文了如指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英文译稿有一定的把控,从而保证了翻译对原作的忠实度。这个模式甚至优于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合作翻译模式,因为他们合作翻译的是别人的作品,而老舍与浦爱德翻译的是老舍本人的作品。
但不幸的是,整部《四世同堂》在美国出版时都被严重删节过,书名也改成了《黄色风暴》(The Yellow Storm)。这样的节译版本应该说是很令人遗憾的。很多作品在翻译成外文出版时都有这样的遭遇,特别是大部头的作品被删节更是常事。还有的译者甚至改写原作,据说《骆驼祥子》英文版的结尾就是美国译者加上去的。严格说删节会给小说造成很大的损失,而改写则是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除非原作者同意译者改写。也就是说,英语世界里的读者读到的《黄色风暴》是经过删节的《四世同堂》译本。
更为不幸的是,老舍先生生前一直没有将中文稿的后十六章拿出来发表。“文革”爆发后,这尚未发表的十六章原稿竟然在抄家过程中遗失了,随后老舍先生含冤投水自尽,稿子再也没有找到。之后出版的《四世同堂》结尾最后三万多字是根据美国出版的英文节译本回译的,就是将这十六章十万多字压缩而成的,看上去颇似一个故事梗概,因此小说是个残本。如果能找到那十六章全部的英文稿翻译回来,无疑其价值要远胜于这被删削的支离破碎的三万多字译文。但过去70年里,那部老舍与浦爱德合作翻译成英文的全译稿并未出现,似乎出现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了。
而这样的奇迹竟然真在最近发生了:《四世同堂》的完整英文译稿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被发现了。从而完整的后十六章英文译稿被复制后带回了国内,翻译后替换原来的三万多字节译本的回译译文会使《四世同堂》终得完璧出版。因为这是老舍亲自参与翻译成英文的,所以说这是最接近老舍原作精神的英文翻译稿。除非将来找到老舍的后十六章中文原稿(似乎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的补译本与原有的老舍中文稿接续出版,应该是目前最理想的全本。
领命进入“老舍状态”
看到这样的消息,我这个老舍作品的爱好者心里自然十分高兴。在这之前几次报纸的荐书活动中,我都是把老舍列在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第一位,我也思忖,谁会获得这样的机会为老舍做翻译呢?我也盼望着读到这后十六章,从而完整地欣赏和学习老舍的作品,还能研究一下美国译者的汉译英技巧。但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译的光荣任务会落到我肩上。所以当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马爱农女士代表出版方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承担这个重任时,我既惊讶又感到荣幸,不假思索就本能地答应说行。
说行,并不是一时冲动之举,也不是仅仅因为热爱老舍作品,而是我认为自己在热爱的基础上有这个学养和实践经验的充分准备。我翻译出版了几百万字的英国文学作品,自己又从事长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与北京有关的就有《混在北京》和《北京的金山下》这样的京味文学作品,以这样的资质,承担这个工作应该是称职的。
但具体到翻译,这次翻译与以前的英译中是不同的。用老前辈杨绛先生的话说,翻译是一仆二主,译者既要对原著忠实,充分体会原作者的用心,领会其叙事风格,做到“信”,还要对目的语读者负责,使译文顺畅通达,也就是做到“达”。但这次“回译”则在一仆二主之外,又增加了第三个“主”,那就是将译文的叙事风格向老舍先生前面的大半部小说靠拢,而人物语言更是要遵循老北京话的风格。这就需要首先正确理解英文原文,正确传达英文稿件的意思,英文理解不能出错,然后在译文准确无误的基础上,在英文本意思的框架内,译者要“扮演老舍”,尽量用自己理解的老舍的口吻讲述故事,用自己熟悉的北京话传达各色人等的对话。
当然这不是说先翻译出一个正确的普通话底本,再进行北京话的润色,这两步并非是截然分开的,真正做起来时应该是两步并作一步走的,随时都要进入“老舍状态”。
于是我抓紧时间把《四世同堂》复习了一遍,划出里面富有老北京特色的言词供自己参考,这才开始翻译。
还原成语俗语 保持京腔京韵
原本以为按照传统小说的做法,《四世同堂》的结尾会有几个故事情节的高潮,最终或许会有十分震撼人心的故事。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最终是以遭到日寇二次关押、受尽折磨、妻离子散的老诗人钱先生的一封长信作为结尾,这在长篇小说中是很少见的,而对这部时间跨度长达数年的战争题材小说来说,其结尾如此平淡、意蕴如此深远,就更是少见。而且其他章节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战争场景,写的是北平小羊圈胡同里普通的居民在战争中的遭遇和从事地下抗日宣传工作,还写了一些汉奸或中间人物的丑陋表演。其叙述语调从容不迫,表现底层人民的感情真挚细腻,讽刺汉奸洋奴入木三分,最终以钱诗人情理交融的谈论战争与和平理念的公开信结束。这样的结尾或许对老舍研究者来说提出了新的挑战,在长篇小说的做法上也有新的独到之处。这样从容不迫的叙述风格与前面已经出版的部分是一致的,那些老北京人包括反面人物的日常言语也应该是老北京话的表达,从风格上说这十六章是可以与前面保持一致的。
有了这样的总体风格的感觉和把握,作为译者,我的任务是前面所说的那两个层面:英文译本是唯一依据,因此要把英文本吃透,不能把表面上看似简单的句子想得过于简单(比如目前传播比较广的一个故事情节,说老舍写那时的北平肉铺供应紧张写得很细致,商人把肉藏在纸盒子里一点一点出售,可这样说的人肯定是读英文原稿时看错了字,把橱柜(cupboard)想当然当成了纸盒子,这就歪曲了小说的基本情节),更不能想当然随意发挥和“改写”。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再考虑小说的京腔京韵,使译文有老舍的韵致。
英文本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很多中文的俗语和成语采取的都是直译法,看上去一目了然。只要你熟悉这些俗语和成语,还原为中文则轻而易举。这让我想到老舍之所以与译者采取直译的办法,是不是有老舍特殊的用心在其中呢?那就是让这些有中文特色的表达法原汁原味地进入到译本中,让英语读者明白中文的表达,从中领略汉语的风采。这种方法后来被教科书解释为翻译的“异化法”,就是部分或完全的直译,给目的语读者以强烈的直观感觉,从中感受异国色彩和情调,甚至久而久之这样的词汇能逐渐进入英文中。如现在很多直接翻译的中文表达法都成功进入了英语词库中一样,比如“人山人海”就直译为people mountain,people sea;“不作不死”则是No zuo no die;甚至“折腾”干脆就是zheteng。估计老舍当年是有这样的考量的。朱光潜先生给老舍写信评论老舍翻译的《苹果车》时,就说过老舍的译文有些地方“直译的痕迹相当突出。我因此不免要窥探你的翻译原则。我所猜想到的不外两种:一种是小心地追随原文,亦步亦趋,寸步不离;一种是大胆地尝试新文体,要吸收西方的词汇和语法,来丰富中文”。朱先生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在具体翻译实践中我们很多人也尝试过适当保留原作的原汁原味,以此来丰富目的语的表达。具体到老舍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英文时使用了很多直译法,与他将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方法是异曲同工的。
这样的例子在后十六章中比比皆是,当然这也考验回译者的功夫,是否能看到英文反应出对应的中文成语或俗语,反应不上来或缺乏中文这方面素养,可能就会翻译得比较冗长啰唆。比如:… your bowels to burst and your brains to be scattered,应该想到是“肝脑涂地”而不是“脑断肠裂”;a woman of the world,应该想到“阅人无数或饱经世故的女人”,而不是“世界的女人”;like a body and its shadow是如影随形,而不是“像身体和影子”;both courageous and intelligent,应该是“智勇双全”,不能翻译成“既勇敢又聪明”。
还有一些句子是彻底的直译,相信这些英文能让我们一眼就看出中文原文来,这样的直译应该说对英语母语的读者来说是直观而新鲜的表达方式,可以从中领略中文的意蕴,如:We cheat ourselves and cheat others,自欺欺人;…palaces with their ancient colours and fragrances,古色古香;…seemed to have crossed out with one stroke of the pen,一笔勾销;to turn the rudder when the wind changed, 见风使舵;等等。
至于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里的北京话还原,我会保留前面老舍的一些表达方式,如“迎时当令”、“电影园”和“呜哝着鼻子”。更多的时候是依据我所熟知的北京话表达方式进行表达。如“绿不叽的脸”形容蓝东阳那张发绿的脸,满口黄牙直打得得(在《北京口语词典》里这个字是口+歹的构词法)表示牙齿上下打战。此外,“打着哆嗦”,“没法子”,“㧟血的勺子”,“窑姐儿”,“活脱儿”,“你的小命儿在我手心儿里攥着呢”,“这要是搁从前”,“踅摸”,“衣裳都溻了”,“舌头好像都木了,动活儿不了”,“硬硬朗朗儿”,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的一些北京话表达,用它们代替那些四平八稳语法正确的普通话,至少是有京味儿特色,让读者感到这个文本与北京的紧密联系。虽然老舍当初用的未必是这些词汇,我还是想在“京味儿”上做一些努力,而不能仅仅满足于把英文翻译成语法正确的普通话文本。
总之,这样的翻译历程是十分宝贵的,回译的过程等于是用北京话进行写作,这对我今后的京味儿文学写作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为此我要感谢这次宝贵的机会,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